时光,不断地把一个人的故乡
换成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故乡,
而一切过程竟很少有人察觉。
一
呈现于眼前的大平原依然如旧,广阔、苍茫,似涣漫无垠的大海,似没有边际又全无方位的时光。但此时,土地上已经覆盖了满满的绿色。茁壮的玉米已经齐膝,随风摇摆,隐隐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密实的水稻如浅水上丝丝入扣的锦绣,断续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即便是农田之外紧靠路边的土地上,也生满了婀娜的蒿草和青翠的芦苇……任惊异的目光寻寻觅觅,竟然找不到一点旧日的痕迹,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怀疑自己迷了路。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啊!百余年前,这里还是清朝蒙古王爷的牧场。数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上,除王爷府为数不多的放牧点、收租点和偷垦者零星分布的窝棚,基本上荒无人烟。很多来蒙荒落户的流民,差不多都有着共同的回忆:一架勒勒车,吃力地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爬行,车轴间不时发出秋雁般凄婉的哀鸣,就算是风吹草低,也还是难以看清远处的景色和方位。直到1926年,“勘放郭尔罗斯西部蒙荒,设官治理”,缓解当时地方经济上的拮据,这片土地才算进入农耕时代。
为了便于操作,“官家”依照中国古代井田制格局,把全境荒地按统一规制分割成大小相等、均匀、规则排列的一个个方格子,每一个方格称作一个“井方”。全境共划出成方的“整井”274个,每井36方,每方45垧;因边界曲折的原因,划出不成方的“破井”35个。“井方”划完后,张作相心生一念,为了给自己罩上一层文治的光环,规定用《千字文》为每一个“井方”定名,按照从北到南,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习惯给每一个方格安上一个字,这个字就成了这一方土地的名字,如果建村,就是村庄的名字。天地玄(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吉林省乾安县最初的行政版图初步形成。
当那篇不连贯的《千字文》念到第13个字时,就到了我的出生地:列字井,那个“辰宿列张”的列,后来因为与宙字井阡陌相连,曾共同组成一个行政村,简称为列宙。实际上,在列字井之前,并没有与千字文一一对应的14个村庄。有一些字比如,荒、昃、寒、冬等被人们认为不吉、不雅的字,没有哪个村庄愿意顶着,便直接弃之不用了。
小时候,在列字井和北边的宙字井两个平原村庄周围,均匀排列着四座巨大的沙丘,因为从远处看,宛若四座低矮的小山,所以我们分别称那四个沙丘为东南山、西南山、西北山、东北山。曾经,我们的村庄、我们的田地、我们的庄稼和我们的乡亲,在遥相呼应的四山之间构筑起我如梦的家园。早晨,太阳从东南山上升起,傍晚,太阳从西北山上落下;春天,风从西南山上刮来,又从东北山上远去;其间有风霜雨雪,有月圆月缺,一场接一场的风沙刮过,一年又一年的流光逝去,一幕连一幕的爱恨情仇交叠,一代又一代的生老病死轮回,我们始终在四山之间,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也始终在四山之间。
 任林举。
任林举。
怀着深深挂念,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表姐夫王广柱带我去看看四山中最高的“东南山”。王广柱是个沉默的人,走在田间小路上一直默不作声。他不说话正好我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和记忆四处搜寻。可是,一路上除了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似乎什么都没有。
“这里就是东南山。”王广柱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蓝色简易房:“那个机井房,就是东南山的最顶点。”
我感到愕然!大地在此处,并没有一点儿隆起之意。如果这个地方就是东南山的话,那个蓝色的机井房下边就是三十年前狼獾的家。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那个直通地下的黑洞在不停地往外冒出冰凉凉、白亮亮的水,而那些虽然有些讨厌但却生动有趣的狼獾们从哪一天起,去了哪里呢?我在王广柱的引导之下,站在田垄之间前后左右看了很久,才勉强看出一点儿大地的不平。就算东南山曾经真实存在过吧!可从前那个形貌昭彰的山,因何变得如此颓然不堪了呢?是因为多年之后我终于长高长大,相对的山就矮了下去,还是因为我自身变得衰老和麻木,不再像童年一样对很多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灵动和敏感?

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和道路都已经不再属于我从前的记忆。时光,如陌上的流沙,掩埋一切,暴露一切,也雕刻一切,它像手段高明的魔术师一样,施展出乾坤挪移大法,不断地把一个人的故乡换成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故乡,而一切过程竟很少有人察觉。
二
穿越苍茫的岁月,我终于看见了从前的我。许多年以前,就在这个叫作列宙的贫寒小村中,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关于他的种种故事和言行,大部分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下来,但有一个形象至今记忆犹新。他就是那样每天坐在课堂的角落里,热切地盼望着老师的提问,因为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把应该背诵的课文背得纯熟,准备着第二天向全班的同学展示一下,但老师始终也没有叫他的名字。这让他有一些失落,有一些怅惘,但他没有气馁,依然坚持每天把应该背诵的课文背熟,然后,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等,他相信,早晚有一天老师会叫到自己的名字。
回首往事,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或人生状态总是不停地在我的头脑里显现。似乎,它既反映了我的性格,也暗示了我一部分命运。
小时候,我就读的学校就是列宙大队那个“小学戴帽”的乡村小学(戴帽学校指,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中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不足,在原来建制不变情况下增设高一级教育班级的学校)。虽然教学水平并不算高,但能够把小学与中学一气儿连读下来。这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就是幸运的了,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每天上下学的跋涉之苦。
据说,有一些地方的孩子上个小学每天就要花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用来走路,而我,却只需要花去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学校。学校是家边的学校,老师也是家边老师,但不幸的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却也是“家边”的水平。
大约是因为我总是会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问老师吧,因为我的存在让老师感觉到难堪,所以老师总是不太喜欢我,因为我是一个“太能钻牛角尖儿”的孩子。面对老师的冷淡,我知道什么热闹的事儿也轮不到我了,于是我就很自觉地躲开人群,有时是坐在角落,有时是站在远处,一个人暗暗地用狠劲,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每一次考试成绩都能够超越别人。
从那时起,无边无际地幻想或阅读一些课外读物,便成为我最好的消遣和“娱乐”。不管什么书,民间故事、古代章回小说,唱本、人民公社诗选、“高大全”小说等等,只要读着就会快乐着,在没有书籍可读的时候,连现代汉语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都要背。
那时的农村生活艰苦啊!人们从春节过后就开始了一年的劳作,运肥,犁地,下种,浇水,三铲三耥,收割,脱粒……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落地摔八瓣,到头来两个给孩子买新衣、糖果的钱都挣不回来。过得好的人家还能维持温饱,过得不好的人家,一到春天就断了粮,需要四处拆借。记得小时候,经常有小朋友吃的玉米面窝头里,掺杂着大量的野菜,咬一口粗粒难咽。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有很强的精神需求。
漫长的冬季来了,北方的大地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一切户外的农业生产活动都不得不停下来。辛苦了一春一夏又一秋的北方农民开始“猫冬”。冬天的昼短夜长让很多精力过剩的农民不知如何应对。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竟然连游戏的工具如扑克、麻将等都没有,人们需要游戏一下,还需要自己动手糊纸板画纸牌,十分艰难。于是,便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找来一本章回体的唱本,找一个识字的人说唱,其他人边嗑瓜子边听书,直到更深夜阑,方才散去。那时,家父是远近闻名的说书人,所以常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本旧小说,交到父亲手上,夜里就会有一群人聚到我家中来。
 任林举(右三)在与家乡农民拉家常。
任林举(右三)在与家乡农民拉家常。
我一边被母亲逼着坐在煤油灯下学习功课,一边魂不守舍地将耳朵挤进人群里偷听。听到动情处,要么流下泪水,要么笑出声来。自然,偷偷听书的行为就会被母亲发现。责备,是肯定要受的,但一般也不太严厉,作为成年人,母亲心里应该清楚,让一个少年人有书不听,不啻于让一个成年人坐怀不乱,要求太苛刻啦!就在这耳濡目染之中,我悄悄地喜欢上了文学。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但我曾在私下里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自己写书,让那些大人读。
其实,我对文学或文字的迷恋还有一方面滋润,那就是我母亲。母亲命苦,三岁丧母,四岁丧父,很早成为孤儿,在她的姨母家长大,自然没有机会读书,但却鬼使神差地读了大半辈子书。她是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开办扫盲班的底子坚持下来的。她平生只两大爱好或者说特长,一是看书,一是教训子女。关于看书,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缝衣做饭,似乎一直手不离书。如果不看书她就会闷得慌,就会止不住地想起痛苦的往事和眼前的烦愁,她就会哀叹不断。为了让她心有所托,父亲和我都曾步行20里去到外村给她借书。直到多年之后,当她偶尔提起某一部旧小说时,我还是不知所从,讲广博,我自叹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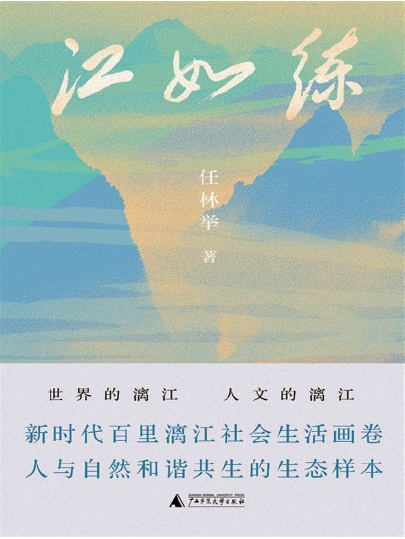
1978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我当时骑在未来的“墙头”之上,面对了左右为难的境遇。是从初中直考中专,还是考取高中后再考大学?在当时,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抉择,向左或向右,都有可能造成一生的遗憾。于是我选择了两条路一齐走,既考中专,又考高中。结果两条路并行了两个月以后,突然拉开了角度,分道扬镳。我手里攥着两张通往不同方向的“通行证”,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上大学的梦想去读中专。因为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我没有赌本,没有胆量和勇气下那笔大注,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稳妥的方案。
当我怀着抑郁的心情坐在长春电力学校的教室里,我想的并不是如何把那些专业课学得更好,而是时时惦记着另外一个领域里的事情。那时,我仍不太懂什么是文学,但最初的文学情结可能已经发酵膨胀。那个时期,除去上课时间,我基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两件事情上边,一是学英语,一是背唐诗、宋词。专业课成绩基本以70分为中轴上下波动,高不过80,低不过60。
在校读书期间,每逢寒暑假还需要回到列宙与父母团聚,但已经感觉到小村离自己渐行渐远了。遇到曾经熟悉的乡亲,人们已经不把我当作本村的孩子了,而是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见面客客气气,关系稍好一点的还要请请饭。不管怎么说,还是能够让人感觉到有一份乡情和温暖在。
毕业分配之后,我到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电力企业工作,彻底告别了故乡,数年之后,我们又举家迁往他乡。本以为家一搬,父母兄弟都离开列宙,此生就不会和那个小村发生什么牵连了。我曾经在内心里怀着十分忧伤的心情与这个小村道别。
三
2004年,经过多年的文学积淀和预热,我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尝试着写一部“有一点分量”的作品。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名作家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什么才是自己最熟悉、最有情感、最牵心动魄的。想来想去,思绪总是离不开15岁之前的那段岁月。后来终于发现,尽管我从15岁开始就离开了故乡,俨然城里人一样“混迹”于各种规模的城市和各种各样的人群,但骨子里仍然没有断掉那条从泥土里生出的根,原乡列宙不仅是我生命之根,也是我的文学之根。

于是,我开始着手创作《玉米大地》,一边以自己的方式重温人在土地上的感觉,一边尝试着唤醒已经沉睡多年的记忆。当过往的一切俱从生命里苏醒时,我发现自己又找到了遗失很久的故乡,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于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在眼前显现:年轻的母亲、逝去的父亲和爷爷、矫二奶奶、张江媳妇、十二舅……奇异的是,从前我还能分清他们谁是谁,谁与谁是什么关系,对我来说孰近孰远,现在我是分不清了,甚至那些庄稼、那些树木,甚至于自己,一切事物的界限和定位都混淆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地上的一切竟然根系相连,血脉相连,万世千劫之后,也许我们将归为一体。
从那时起,我开始深刻地思考土地与庄稼、土地与农民、农民与庄稼之间的关系,思索着为什么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滋养了一茬茬生命之后,仍然得不到赞美和感恩?为什么历经了种种悲伤、疼痛、无奈、苦难之后仍然如大地一样沉默无声?难道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这一系列苦命的事物,我无法继续躲在角落里只想着自己的心事。我感觉到有一种隐约的使命在呼唤着我,一步步引导着我走向我生命的起点。当我的情感与灵魂一贴近大地,我的个体消失了,不知道是他们消融在我的生命之中,还是我的生命消融在他们之中,我感觉到自己变得通体光明、力量强大、富有激情,我感觉我就像懂得自己一样懂得他们。从此,我将代表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声音。
25天之后,当我以一种火山喷发的方式完成这部作品时,我感觉整个人,气血以及情感均被消耗一空,我无力地伏在案前,连重看一遍,修改一遍的力量都没有了。之后的数月之间,我连一个字也写不成,恐惧时时地向我袭来,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一只作废的火药桶,再也喷不出激情的火焰?
2005年3月,我去了鲁迅文学院学习,把我的作品拿给那些评论家同学看,同学们激情澎湃,有十来位同学为这部作品写了评论文字,但每一个同学的评论我都没有看全,因为每一段贴近心灵、触及灵魂的文字都会让我感动流泪,因为我的“内伤”尚未痊愈,仍很脆弱。
接下来的作品是系列散文《松漠往事》,这是《玉米大地》真正的姊妹篇,无论在风格上还是情感上都承接了《玉米大地》的气脉,并且由于结构的相对疏散,使每一个篇章的伸展更加自如,语言、语调和情绪上也就更加隽永。只可惜,这部作品出版之后,由于没有推介,缺少宣传,便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很快便被当作一块丑石弃于人声鼎沸的街市。于是我就劝自己,还是把它忘了吧,就像极力忘却自己的一份烦恼。
进入《粮道》的创作时,我虽然将视野从故乡转向全国,从乡亲转向普遍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但究其根本仍然是基于过去对故乡农民的了解、理解和同情。后来《粮道》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我觉得当时我最应该说的一句话仍然是“感谢故乡给了我生命之根,也给了我最珍贵的一段人生经验。”谁让我写了粮食呢?只要是粮食都是我在列字井认识的粮食。

阔别之后再回乡,这个一直被我称作故乡的小村,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模样。随着农业生产力的逐年发展,农机和农业科技水平逐年提高。原来以土地盐碱化、气候干旱著称的列字村,如今都用上了滴灌技术,旱田变成了“水浇田”,大田产量直线上升,由原来的亩产不足千斤跃升至1500斤以上;大片大片的草甸子也被开发利用,昔日寸草不生的碱泡子或长满了碱蓬草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绿色的水稻和白色的水鸟相映成趣,远看,宛若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县乡两级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扶持下,集体发展葡萄产业,家家户户种起了大棚葡萄致了富。到2023年末,列字村的葡萄大棚数量达到400栋,主导产业收入过千万元,仅此一项,就使村农民人均增收达到了26700元。由于列字村鲜食葡萄的闻名遐迩和供不应求,让乡里和县里作出了更大、更加宏伟的发展规划,他们正谋划在条件具备和政策支持之时将周边几个村庄地字村、辰字村、张字村、宙字村、元字村的村民都集中搬迁到列字中心村,打造一个声誉更高,产能更大的“葡萄小镇”。
明知道这个一别多年的村庄已经远远不在我的记忆中,但我仍像归家的孩子一样,怀着好奇和喜悦的心情问这问那,好像事事都与自己有关。之后,又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发问:“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当然没有人回答,但我心自知,它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情感里。
(陆朵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任林举

作者简介
任林举,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个人著作近30余部,代表作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瑞雪丰年》《此心此念》《出泥淖记》《虎啸》《江如练》等。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蒙等多种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等。





 投诉侵权
投诉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