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成为了我致力的事业,
那既是我兴趣之所在,
也是使命之所然,
而其渊源却可追溯到故乡的那方山水。
我的家乡云南省梁河县是靠近缅甸的多民族地区。老家叫孟连村,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傣族。汉人奉祖先规制,傣族行夷人传统,各行其是,数百年和睦相处,可谓典型的“民族团结村”。
孟连村坐落于梁河县大盈江西岸的河西台地上,和当地所有村寨一样,寨头有百年榕树,数十座土墙瓦房相拥聚集。一条清澈小沟从村中潺潺流过,村外稻田环绕,村中炊烟袅袅,静谧如画。白驹过隙,数十年一晃而过,然而少年时代的家乡记忆——农村艰辛的生活、淳厚的民风民俗、古朴的节庆仪式、亲和的人际关系、诗意的田园风光、巧妙的生存技艺、采集渔猎的奇趣乃至山茅野菜的酸辣苦甜等,却时常浮现脑际,恍如梦境。

尹绍亭。作者供图
“乡愁是一首歌,乡愁是一杯酒”,这首“歌”、这杯“酒”,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世事难料,后来进入学界,乡村研究成为了我致力的事业,那既是我兴趣之所在,也是使命之所然,而其渊源却可追溯到故乡的那方山水。
一
我的乡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读研究生之时。开始是以生态人类学理论为参照,调查研究当代云南热带、亚热带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其缘起及其经历,在我所著的一本专著的后记里有如下记述:
我写刀耕火种,也许是与其有缘。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滇西的一个小镇度过的。那里的地望过去称之为腾越,史家说,那是古代越人的故地。小镇很多人家的家谱上写着,他们的祖先原是南京府人氏,系明代三征麓川时随军迁到云南来的。而文献记载,其时腾越还分布着“枕山栖谷,以便刀耕火种”的阿昌和“居住高山,刀耕火种”的傈僳等民族。古代江南汉族迁至腾越后,当然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然而也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那里几年前还能看到汉族独特的刀耕火种之法,就是一个明证。

那是森林消失之后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残余形态。人们以锄或犁翻起长满杂草的土垡,将其垒成一个个圆形土堆,内燃烈火,外覆土块,其状犹如蒸笼里的馒头。
大约是在我九岁那年,学校组织郊游,期间有红蓝两队争夺红旗的游戏。一面火红的旗帜高插于山岗翠林之中,两队人员同时从山麓两侧向上冲去,率先夺得红旗的队即为胜者。其时我年龄虽小,但不甘示弱,与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奔跑在前。当接近红旗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地中垒着无数丝毫看不出燃烧痕迹的土堆。眼见对方人员冒出山林向红旗冲来,心中着急,干脆踏土堆直跑吧,于是一脚踹入了土火堆。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是夺旗成泡影,皮肉却大吃其苦,从此留下了一脚刀耕火种的斑斑花纹。
后来离别了故乡,对于刀耕火种也便渐渐淡忘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生态环境问题突显,热带刀耕火种成为世界环境热点,报道文章连篇累牍。久违了的刀耕火种不再是脚上的疤痕和中学时代的记忆了,突然令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山地民族为何不种水田要行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是否是“原始陋习”?刀耕火种为何屡禁不止?时代需要回答!
于是不顾艰险,以其为己任,一头扎进乡村,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十余年间,我走遍了大半个云南的村村寨寨,许多村民伴我翻山越岭、走村串寨,进行采访调查,大受其累。一些村寨作为我深入观察体验的基地,我与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感情。
刀耕火种是什么?为何屡禁不止?通过研究,我向社会和学界交出了答卷:当代刀耕火种是热带、亚热带山地民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它是一个以多种轮歇方式为基础,以村社制度体系为保障,以万物有灵世界观及其仪式体系为调适机制,包含土地认知、土地制度和管理、作物多样化及栽培技术、作物轮作混作、粮林轮作等知识技术的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在工业社会之前人少地广、远离市场的偏远地区,刀耕火种的存在具有难以替代的合理性。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在全球化、人口增长,资源紧缺、重视环保、强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刀耕火种以森林换取粮食所表现出的粗放、高耗、高碳的生产形态,暴露了其适应的严重缺陷。不过,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赖以生存的食粮生产方式,要改变它就必须有新的生计形态。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不具备生计改换的条件,所以“屡禁不止”。刀耕火种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说明经济问题只能按经济规律运行。
作为刀耕火种的研究成果,拙著主要有《云南刀耕火种志》《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等,以及《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等中、英、日论文报告二十余篇,其中多个被评为省部级优秀著作奖。
二
1989年我调到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副馆长,经常带领年轻馆员到田野调查,收集文物和展品。从山地丘陵到河谷盆地,从热带雨林到雪域高原,走过无数村寨。

在乡村调查过程中,各民族的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多样性,时时给人以刺激和惊喜,每天都有新的知识和收获。民族文物和展品的征集,涉及农耕、服饰、艺术、节庆、饮食、宗教、礼仪、古籍、交通、建筑等门类,每一个门类,又包含多个种类。民族文物和展品的征集,既是博物馆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作。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农耕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相应的物质文化也随之变化和消失,如果不及时征集收藏研究,今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1991年秋天,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来中国调查。唐立为科技史专家,曾参与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糖史”的写作。我们在昆明见面,唐立认为中国榨糖机只有直立式双滚轴榨糖机,我告诉他傣族有直立三滚轴榨糖机,唐立非常肯定地表示不可能。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古代文献从来就没有过直立三滚轴榨糖机的记载,二是这种三滚轴榨糖机只存在于印度及其周边,属于印度文化圈范畴。我不与他争辩,翻出在田野里拍摄的三滚轴榨糖机的照片,唐立看了十分惊讶。我告诉他那是在临沧地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孟定傣族村寨拍摄的。
1989年10月,我去滇西南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调查。一天傍晚,调查随行的一位傣族大哥不经意地说起河那边的甘蔗地里有一台榨糖机。我听后立即提出要去看,其时天色已晚,傣族大哥面有难色,但我决意要去。就这么一坚持,碰上了珍贵资料,绘图拍照忙活了半天,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种三滚轴榨糖机。让唐立更难以相信的是,我告诉他傣族不仅有木制的直立三滚轴榨糖机,而且还有水力驱动的卧式弧形齿双滚轴榨糖木机。唐立说,水力驱动的卧式榨糖木机不仅未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就是在亚洲其他曾经有过的地区,也早已消亡无迹了。如果真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奇迹。
为证实我的说法,唐立次年又专程来云南调查。我带他前往之前在西双版纳州调查的傣族村寨去看,不料才短短两三年时间,该村的水力榨糖木机已不见踪影,所见竟然是电动机械了。唐立十分失望,我亦非常沮丧,幸而后来到别的村寨看到了水力榨糖木机,这才证明了我之所言不虚。后来唐立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这一新的发现,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的不足。
再有便是关于传统木犁的调查研究。国内研究木犁的学者不少,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木犁的起源,二是木犁的进化演变。关于木犁的进化演变问题,国内多数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木犁的进化,最早是“耒”,继而演变为“耜”,后来进化为直辕犁,最后演变为唐代江南的曲辕式“江东犁”,至此定型,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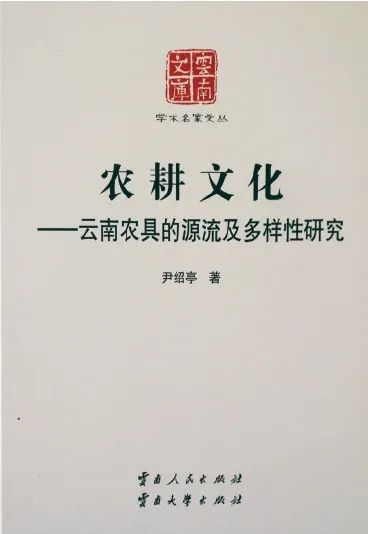
我调查木犁,跑遍了云南及其周边地区,收集了近两百份标本资料,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云南木犁种类十分丰富,多样性十分突出,这是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云南可以说是一座活态的“木犁博物馆”。第二,云南木犁,地域和民族特征十分显著。滇西北的木犁与南亚和黄河中上游流域的木犁类似;滇池地区的木犁与江南和中原的木犁有渊源关系;滇西南的木犁与华南和东南亚的木犁同类;元江流域和滇东南的木犁具有本土特色。地域和民族特征如此明显,说明木犁类型多样性的形成乃是各民族对生态和风土的文化适应和文化选择的结果,而非如某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进化系列。第三,综观云南各民族现实使用的二十余种类型的木犁,绝对分不出谁比谁早、谁比谁晚,谁是谁的原始形态、谁是谁的进化形态。所以,学界盛行的“直辕犁一定要向曲辕犁演变,最后成为‘江东犁’”的“定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应该予以修正。
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我主编了几种著作,其中《云南物质文化》丛书影响最大,一度畅销。《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为我所著,出版后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学界反响热烈,日本东京著名学术出版社“第一書房”很快将其翻译,并在日本出版。2011年我受邀访问法国汉学中心,也是因为这本书的原因。
三
1997年,有感于乡村传统文化急需保护、传承和弘扬以及乡村振兴的需要,我策划了“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什么是“民族文化生态村”?我们的定义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场景中,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
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意在探索地域和民族民间文化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途径;从学术的角度看,是以人类学为核心的多学科结合的应用研究的新课题;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看,则可为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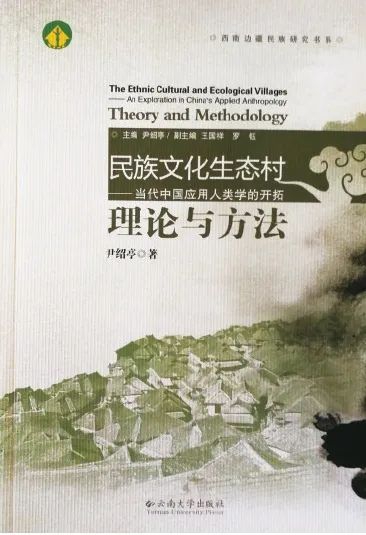
199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发展战略,“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被列为重点项目,我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第一批选择了五个试点——腾冲县和顺乡(现腾冲市和顺镇)、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村、新平县腰街镇南碱村、石林彝族自治县月湖村、丘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村。项目从1998年10月开始至2008年10月分三期进行,历时10个春秋。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通过10年建设,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诸多社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试点村村民和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和顺属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位于县城西南4公里的一个小盆地边缘,是著名的“侨乡”。村落依山建筑,山涌清泉,河流环绕,田畴相望,风景如画。腾冲县与缅甸山水相连,是古代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蜀身毒道”的要冲,两国边民自古交往密切。数百年来,包括和顺人在内的腾冲人“穷走夷方急走场”,每遇困顿厄难,即往缅甸谋生,富裕之后,则尽力支持家乡建设。和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历史建筑精粹,有不同于一般乡村的发达的教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在海外艰苦创业的乡亲。
和顺现存寺庙宫观殿阁八大建筑群;宗族祠堂八座;村中有建于1924年、为中国乡村最大的图书馆——和顺图书馆;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故居纪念馆以及乡贤寸绍春于1921年兴建的绍春公园。和顺现存一千余幢汉式民居,其中经典的传统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四合院、多重院以及中西合璧建筑尚存一百多幢。此外,还有文笔塔一座,石拱桥六座,洗衣亭六座,闾门牌坊十六座,月台二十四个等。以上仅为和顺的建筑文化遗产,其非物质文化的积淀,也是一般村寨远远不能相比的,所以和顺素有“极边第一村”的美誉。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数十年来和顺曾多次遭到摧残。主村落中的七座标志性的高大石牌坊被捣毁,宗祠的牌位、柱标等被拆除,宗祠、寺观、民居的大量匾额、楹联、雕刻也遭到严重破坏,许许多多珍贵文物被毁弃、焚烧。生态环境方面,部分水域、湿地被填为水田,山林也频频开垦为农地,受工厂污水、黑烟和居民生活垃圾的污染,昔日清澈的河水变黑发臭。尤为遗憾的是,部分村民不再珍视文化传统,盲目拆除传统民居,乱盖、乱建钢混结构楼房,严重破坏了村落景观和生态环境。几经磨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顺的情况始有转机。为了唤起社会和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重振和顺人文精神,再现侨乡历史光辉,我们将和顺选为第一批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试点。

项目组于1999年12月10日在和顺正式成立工作站,省、县两地的项目组成员互相配合,做出很多努力。我们对乡史、侨史、商贸史、环境史、建筑史、抗战史、乡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宗祠文化、社团文化、饮食文化、楹联文化、民间艺术、婚姻家庭、风俗习惯、文物古迹、教育、历史名人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从该乡的各类建筑和文物古迹中,筛选出九十余项。在悉心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中英文的简要说明,提交政府有关部门,树碑立牌,制定管理措施,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进行管理和保护。同时,对具有代表性的寺院、宗祠、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进行测绘,获得了大批宝贵的实测图,这为该乡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规划、保护、开发提供了详细资料和科学依据。
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调研成果展览以及不同形式的座谈会,以此加大文化遗产宣传。为了弘扬和顺的建筑文化遗产,项目组借用该乡李氏家族名为“弯楼子”的老宅和大量生活用具建立了“弯楼子民居博物馆”。馆内除了复现弯楼子昔日的建筑风貌和文化氛围之外,还设立了“悠久历史”“著名侨乡”“建筑集萃”“极边名村”四个展示专题。该馆开馆之后,吸引了大量中外游人前往参观。
最值得关注的是“和顺人写和顺”计划,我们组织12岁至90岁村民数百人,参与撰写本乡的历史文化,成果集结为《中国最具魅力名镇和顺研究丛书》(乡土卷)(华侨卷)(人文卷)三卷本。出版之后,反响热烈,海外的乡亲们都说“是实实在在为和顺办了一件大好事”。随后在保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策划编写出版了多本与和顺有关的书籍,为和顺古镇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村落文化遗产资料。
2005年,和顺在全国众多名村名镇的激烈竞争中,斩获了“中国十大魅力名镇”、夺得“中国魅力名镇展示2005年度大奖”。2024年,和顺又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再来说仙人洞村。仙人洞村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为彝族撒尼人村寨。该村喀斯特地貌典型,山峰不高,一座座形如石笋,拔地而起,奇峭秀丽。山峰之间是宽阔的湖泊,湖面如绸似缎,清流舒缓,菏苇摇曳,村子靠山临湖,景致十分优美。然而,在1999年以前,仙人洞村却是一个非常贫穷、脏乱的村寨。“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破烂不堪”,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针对仙人洞村的情况,我们和村民一起分析本村文化和生态资源的特点,找准重点,确定目标,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和近期具体行动计划。通过理念培育、能力建设、技能学习等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性。建设期间,制定新的村规民约和行为规范,大力整治环境,消除脏乱差现象,绿化环境,建设绿美家园。发掘文化资源,恢复、传承、活化、赋能传统文化。同时举办“篝火歌舞晚会”“民族赛装会”“旅游节”“荷花节”“花脸节”“辣椒节”“对歌节”等活动,并新建民宿旅馆,开发特色美食,发展优质旅游业。
环境变得干净优美了,文化富于特点,游客量持续上升,年接待数十万人,村民收入大增。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之前,村民年均收入不过300余元,如今上升到4万余元,增长了100多倍。年收入十几万元的人家不在少数,部分人家年收入甚至超过百万。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仙人洞村不仅成为了小康村,还斩获了“民族团结示范村”“国家级精神文明村”等,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榜样,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2008年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结题,我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退休,依然时时关心乡村的建设和发展。2018年2月6日,我应邀参加基诺族“特懋克”节日庆典,见到交往近40年的基诺长老和文化传承人,傍晚喝酒畅叙,写下小诗一首。兹录于下,权当本文之结语吧:
农耕研究成往事,生态乡建有新篇;
乡村留得情谊在,入夜把酒忆华年。
作者:尹绍亭
作者简介:
尹绍亭,1947年生,云南省梁河县人。云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创新基地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参与领导建设云南民族博物馆,主持建设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和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以及多个民族文化生态村。
著作有《人与森林》等中、英、日文专著十种,主编《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等丛书十余种,著有《生态人类学》等译著,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多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图书奖、云南大学伍达观杰出教师奖。





 投诉侵权
投诉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