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跌宕起伏的时间洪流下,在作家对故乡命运的忧愁与悲喜中,时代的列车已拉响鸣笛,势不可挡。
出生在哈尔滨,一直在这里生活了40年才离开的贾行家,十分不“东北”。如果说,身材魁梧,肢体动作丰富,张口闭口“哎呀老妹儿”式抵挡不住的热情,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东北男人形象的话,那么上述所有状态的反面,便是贾行家。
 贾行家
贾行家
因此,当“反面”东北人贾行家拿起笔,他笔下的东北注定不是“有山有水有树林,老少爷们很合群”式的轻松幽默,也不是叱咤春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东北小品的欢声笑语,而是完全颠覆着人们对东北的最初印象。虽然形象不“东北”,但他却一直跟东北“同呼吸,共命运”。享受过“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失落过东北的“辉煌不再”。但当所有的失意在笔尖流淌时,恰好汇入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洪流。当痛苦被书写、被看见,开始引人反思,东北也在注视中疗伤、复原、崛起。在跌宕起伏的时间洪流下,在作家对故乡命运的忧愁与悲喜中,时代的列车已拉响鸣笛,势不可挡。
哈城人的骄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出门去北京、大连或是其他一线城市,哈尔滨人并没有那种到了大城市的感觉。那时候一线城市有的,哈尔滨也都有。反而可能在一线城市的人眼中,这些穿着貂皮大衣、举止阔气的东北人,更像是“大城市人”。
这看似优渥的生活并不是装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多家国有企业集聚,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单是在哈尔滨,就拥有名扬全国的“八大军工、三大动力”,五千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也有二三十家。大型国企承担着职工们的一切生活资源和发展机会,在“包办”体制下提供全方面的社会服务:厂幼儿园、厂医院、厂公安局,甚至是厂电视台,一切都要打上厂的烙印,职工们的一切都围绕着厂区展开,生活的半径就是厂区的大小。
 2005年12月4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居民走过冰冻的松花江,背后是正排放废气的烟囱。
2005年12月4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居民走过冰冻的松花江,背后是正排放废气的烟囱。
贾行家的父亲是原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所在的“哈飞”,工厂面积大,“号称有八千工程师”。当时还是孩子的贾行家依稀记得一个场景,如果一大家人全都在厂里上班,早上出工必定穿戴齐整,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走到他面前会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那种脸上“亮亮”的表情,直到成年后的贾行家才明白,那或许是国企赋予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之下的优越感。之所以难忘,是因为从贾行家慢慢开始记事之后,这样的表情在很长时间就没有再见过了。
到了星期天,大家还会拿着吉他,拎着用塑料袋装的散装啤酒去太阳岛享受周末的阳光。在那个年代,塑料袋还是很高级很罕见的,因为它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一般人是没有的。“就像今天背了一个名牌包一样。”贾行家的脑海中有些画面记忆深刻。去往太阳岛的车上总是特别挤,家家大人都背着大书包,斜插着两柄雨伞,抻着脖子向车窗外的北面看,嘴里“嗯啊”地答应着孩子的吵闹。防洪纪念塔一带,有放风筝的,滑旱冰的,举着贴满黑白照片的牌子来揽生意的,钓鱼的,河漂子一样游水的,洗衣服的,真的是游人如织。
冬天,孩子们除了在冰上玩,还会舔铁,“一舔上去舌头就一粒一粒地粘上面了,能清楚地感知到舌苔是颗粒状的。然后再一粒一粒往下揭,揭的时候就觉得嘴里有血腥味了,不知道那是冰铁的味道,还是血液的味道。”
贾行家的姥爷是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也拥有极致的浪漫。周六晚上带着一把两侧镶着白铜雕花,枪托用油亮的枣红木制成的双筒猎枪,随意跳上一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车,去深山里打猎。周一一早背着大兴安岭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鸭子,有时还有长着獠牙的猪回来。要么就周六坐着火车去钓鱼,回来之后咕嘟一大锅鱼,上顿下顿,连左邻右舍,一起吃到礼拜三,很是惬意。
失去光鲜亮丽
这种惬意是何时消失的呢?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尽相同。在一位村书记的印象中,他有天突然发现,好多绥化的城里人突然跑到集上来买苞米面了。“这是出啥事了吗?”他心里嘀咕。大人世界里的事,大人从不主动跟小孩子说,可贾行家还是察觉出了异样:过年的时候,精气神变了。“哪怕他们穿着貂皮大衣来拜年,你也知道那是借的,但我也不会揭穿,因为心里还是很难过的。过年大家装也要装得很体面,可那时候他们连装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到世上来,仿佛就带了双眼睛似的,只管东张西望,没有承受和创造过什么。看人总是偷偷摸摸的,找个角落,躲开对方的目光,常不慎窥到别人不愿被见到的。”贾行家回忆,就像他小时候,常常是趴在屋外的窗沿上,看屋里发生的一切。如果是冬天,窗户上凝结了一层雾气,贾行家总是用手擦干净一小块,看向屋里热气腾腾,脸上却挂着霜的大人们。
小孩子突然撞破了大人世界里的秘密,童年的明亮多了一抹暗色,从玻璃窗外看进去,像是屋外的寒气进去了,往年热气腾腾的氛围冷了下来,屋里和屋外似乎不再是两个世界。
“非得给人制造一个情境,才能看到人是什么样的。”在贾行家看来,这个情境就是工作没了,机会在消失,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却无处伸张。那些原本被东北一代们用来铸就体面自我的东西:铁饭碗、高收入、大集体的优越感……正一步步瓦解,堆砌成的“自我”自然也就成了一地鸡毛,就像契诃夫在《装在套子里的人》里塑造的别里科夫一样。装在套子里的人,肉体与壳子已经长在一起,当有一天,壳子碎掉了,只剩下柔软的躯体面对冰冷坚硬的世界。这时已经谈不上低落了,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他们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是接受失去那个光鲜亮丽“自我”的尴尬。
 火车驶过玉米地。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照。资料图
火车驶过玉米地。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照。资料图
见多了这样的尴尬,贾行家慢慢地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具有悲剧底色的眼镜,小时候偷窥到的秘密埋进心里,慢慢地又在充满“悲剧”的处境中发了芽,等到成年后,才有机会讲给世界听。贾行家能够理解这些“东北一代”们的痛苦,“根源在于拥有后突然失去,并且决定权从不曾在他们手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具备早期典型悲剧人物的特性——强力抗争,却不得而终。而对于他自己,他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些人,“遇到一个事情,我会习惯性地从来不会看到好的一面,时间长了,已经没有像样的愿景。”
选择向下看
贾行家的父亲高考时考上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哈飞”,成为一名工程师,这个群体,是“最有希望、最让人羡慕的一群人”。“哈飞”在哈尔滨的命运也是幸运的,虽然所谓的“八大军工,三大动力”的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解散,但“哈飞”在改制中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贾行家的家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或许还能按照父亲的路径走下去,但他终究还是渐渐长成了不同的样子。“从小就自卑,学习不好,什么都不行,中学里用五六年的时间都在看杂书。”那时家里的旧书极多,倒不是“家学渊源”,“一块钱一本在摊儿上淘的,还盖着某个工厂图书馆的印章。”
叛逆的少年在属于他的时代又碰上了时代的热潮——摇滚乐——它击中了一个孤僻少年的心脏。他花几千块钱买了吉他,日夜痴迷于最终半途而废的摇滚乐。“那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很胆怯,但内心的桀骜不驯已经生长起来了,处处看着都不满意,处处都愤怒。”这种桀骜不驯并没有让贾行家的自我变得膨胀,还是能够放下自我去观察,“我想搞到一个说出来很好玩,但其实全无实际用处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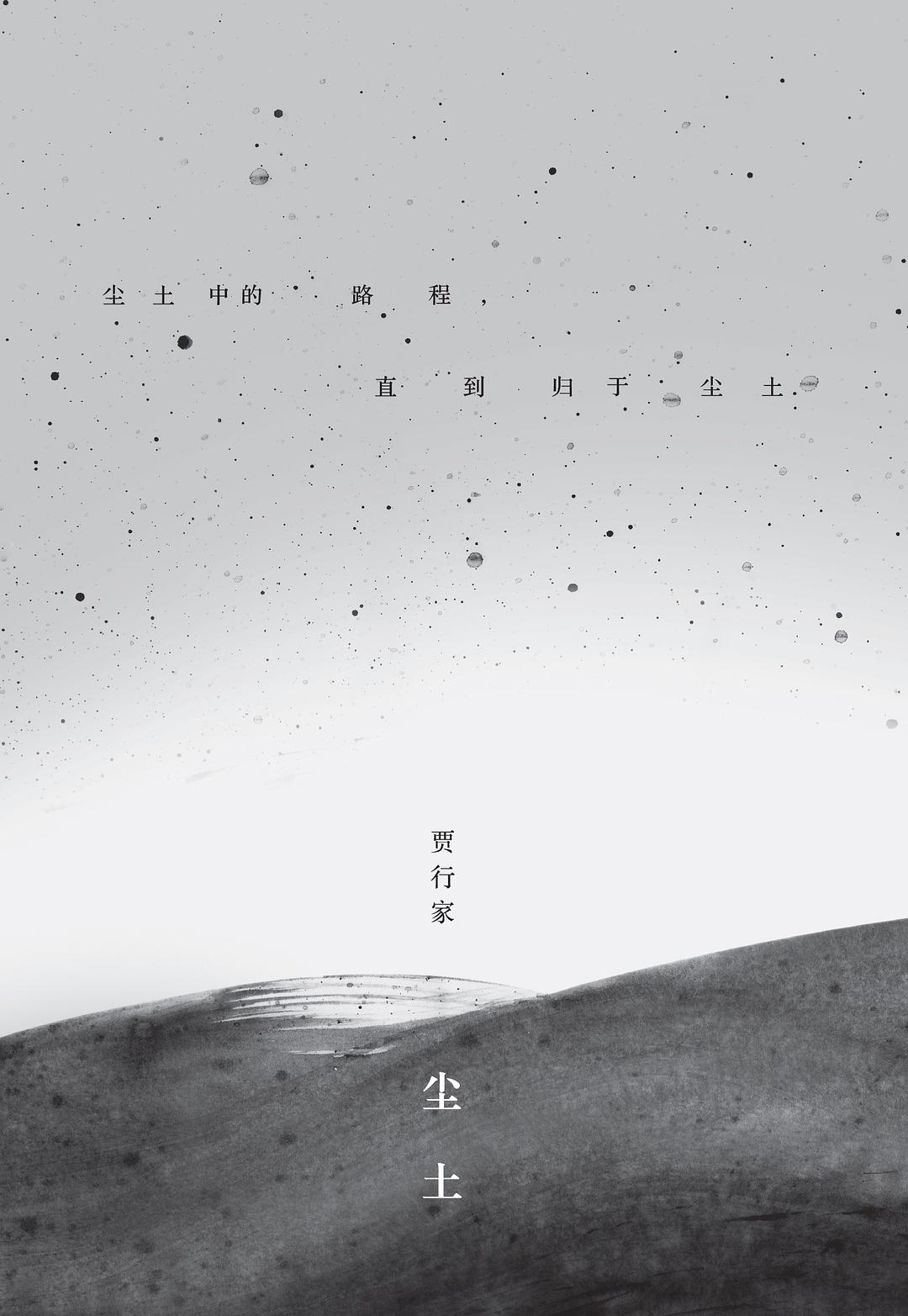 贾行家作品封面。
贾行家作品封面。
长了一双可以向上看或者向周围看的眼睛,但贾行家却选择向下看。可能是因为看向周围的时候,贾行家总觉得这些人的行为都是社会规定好的,“但我又不擅长去实现那些社会规定的目标,比如好好学习之类的。所以更愿意跟更自然、更诚实、更热情的人交往。”再加上贾行家从小就喜欢写东西,“就天然地觉得他们身上有故事,即使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也觉得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人的经历,他们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
因此,或是自觉地,他把目光从附近转向了更广阔的小人物的世界。“只是眼见他们各自背负命运,小心翼翼地活成生活,有的最终交付了出去,有的仍然打碎了,使我不得不庄严。”
在贾行家的记忆中,老城里的一些聚处,是尘世气息最炽烈顽强的地方。北三菜市场几百步,每个摊子都有点来头,从南头进来,左面卖瓜子干果,右面卖煎饼,向前是几辆塑钢窗围成的流动车,卖海产和蚕蛹。有家温州人开的菜店,叶菜都叫不出名字,也不懂得吃法。还有专做天津果仁的,现杀活鸡鸭的,做槽子糕的,卖牛羊肉下水的,炸鱼烀狗的,切面铺,熏酱点,澡堂子……挤得中间只容两三人并排,冬季下水井口结了很高的冰,走起来更慢。
小时候的贾行家老爱去这里玩,不仅是因为这里热闹,历史悠久,还因为市场尽头的一户人家里,住着他的好朋友李晚黎。而爱去他家的原因是:他永远在家。李晚黎两岁时被一口热汤毁掉了整个呼吸道,挺过来后,肺只有五分之一还活着。他的胸前有个不愈合的创口,到了秋天,要插一根管子进去,他终生只能朝一个方向侧着身子睡觉。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不太健康的人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对他从来没有同情之类的情绪,也并没有珍惜过自己的健全。”长大后的贾行家再去回想这段友情时,觉得它满足了自己对不同人群天然的好奇。“就觉得他身上、他所居住的老街区聚集了我们时代的底部。”在贾行家看来,时代是沉积式发展的,越往底部沉积越多。那些野生的,具体的,丰富的,或者说杂乱无章的,都汇集到了底部。而底部独有的市井的、温柔的记忆,他觉得最宝贵。
但随着朋友的去世,市场的拆除,兴趣也随之失去了容器。以前的北三市场,很多两代人守着一个摊位,什么东西都买得到。可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老字号了,包括早餐店。”
贾行家常常回忆,昔年街巷里居住着的人家,会在不大的小院里种开花的树,窗台再养上几盆山茶和吊兰,“老两口互相比着,谁的花开得早、开得久。”
乡村印象
2017-2018年间,来北京之前的那个冬天,贾行家在黑龙江找了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白雪覆盖之下的广袤土地,那时是最好看的。”他吃惊于为什么房前的小院里只种菜,没有一个种花的。“其实旁边广阔的农田到处种的都是菜了,为什么不能种点花?”
在贾行家之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关于东北乡村的印象更多是属于二人转和东北小品的,喧嚣的热闹与开心,铆足了劲要逗人乐。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东北地域文化的潮流席卷全国的程度。那时,《刘老根》《乡村爱情》等影视作品代表着东北农村的表达。
贾行家自认为对乡村甚是无知,用的也是最浅薄的旁观。在村子待着的这段时间,贾行家记录了很多村里人的故事,说是记录,贾行家认为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虚构与想象。在自言自语中潦草地记下了一些片段,这些只言片语,看不出一丝一毫外地人眼中曾经熟悉的、幽默的、俏皮的东北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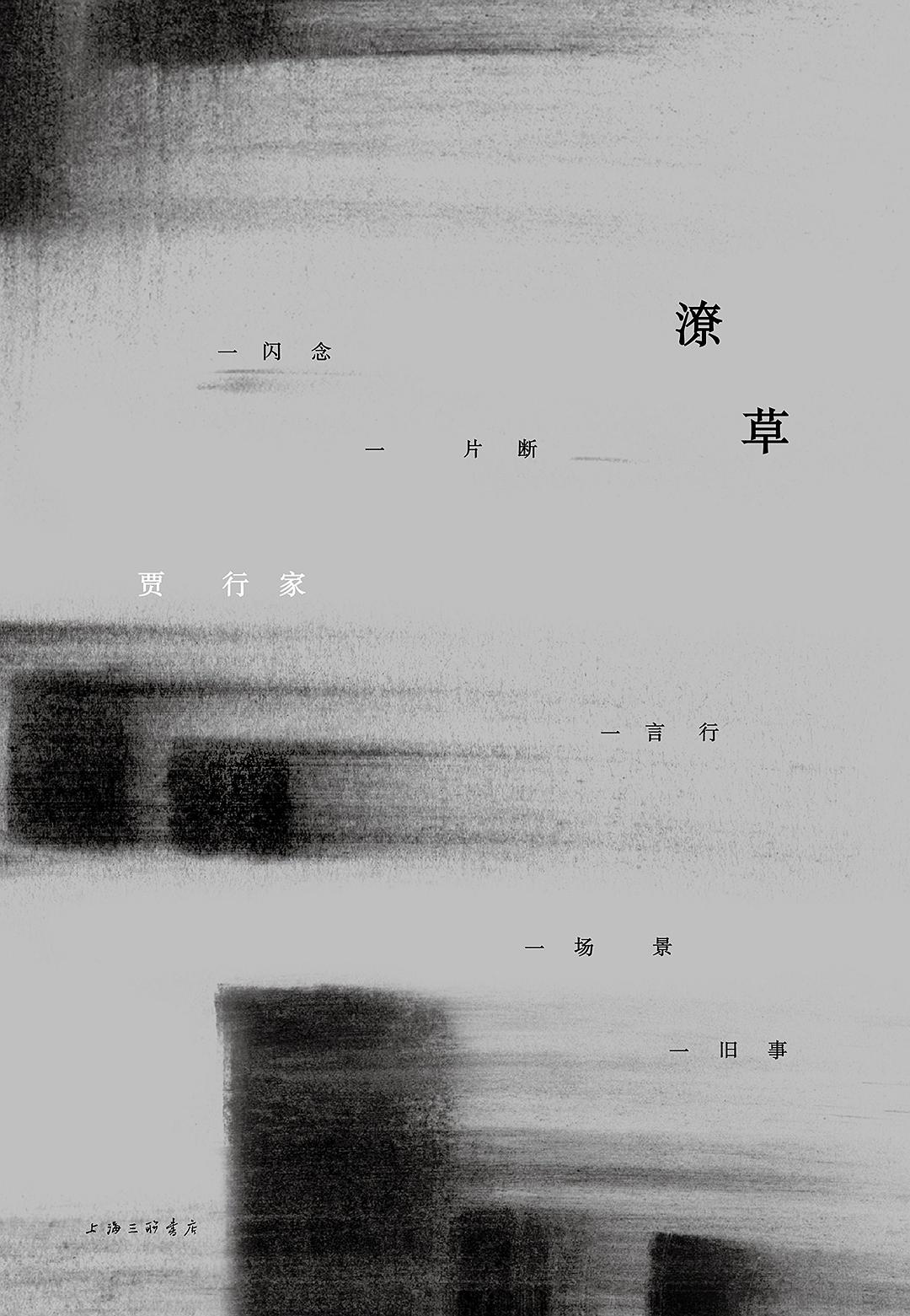 贾行家作品封面。
贾行家作品封面。
来村子之前,他听说,在村里,除非残疾或者孤寡无劳力,吃饭穿衣总不成问题的,然而等一段乡里时间过完,他的旁观多了一点深刻。他观察到,一些村民好像处在一种“只在这儿住一阵儿就走的状态”,房子只要勉强能住就行。贾行家能够理解,那可能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毕竟农民一年到头手里现金有限,吃的是地里种的,取暖烧苞米秆子,能不多花钱就是最好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种花的原因吧。”
他也总是会注意到村里的边缘人,“有一个人,每天放两头牛进山,剩下的时间就坐在屋里看房后的几个大风车,那些风车都是他自己安的,有三米多高。”贾行家不觉得这些无意义,反而觉得这是有趣的事情。而之所以能“看见”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少数对我有兴趣的人”。
“很多人把乡村乌托邦化,只是把自己对‘生活在别处’的需求放在了一个想象的地域中了。”贾行家不知道,这算是明显的废话还是不该说的冒犯。
另一个东北
来到北京之前的贾行家,经历了6年警察和11年行政单位工作的生活,“最有活力的小半辈子都在东北”,一直挺满意,想一辈子做一个躲着“写日记”的人。他以“阿莱夫”为笔名,在无边无际的互联网世界里兴之所至地写了十几年,讲述的主人公,大都是故乡的人,“毕竟我一直身处其中,清清楚楚地知道发生的事情,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他们都活过。”
但挺突然,贾行家说辞职就辞职了,毫不珍惜现在年轻人挤破头也想跨入的门槛。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叛逆,他总是向着时代潮流逆行,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时代总是迎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他却偏要成为那个执拗的低音,向后看,向下看。
虽然他不肯承认自己在写作上的天赋,但还是收获了不少支持。剧作家李静说他的文字“只读第一个句子,就感到来者不善,单刀入阵,寸铁杀人”。作家梁鸿说他“老辣而不世故”。媒体人东东枪则说:“他就像个值得千里迢迢去拜访的贤人,你去的时候,他可能正在午睡或垂钓,也可能是个樵子渔夫,正忙着劳作,跟你聊会儿,还得登山涉水去。”
见证了父辈事业暗淡的贾行家,和包括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作家在内的“新东北作家群”开始集体写作,将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市场经济转型后所经历的“阵痛”记了下来,在这些东北往事里,不吝笔墨地诉说着被时代、社会忘记的边缘人物的故事,让读者看见了另一个东北。东北的文艺开始“复兴”,“有山有水有树林”换了种形式回来,变成了《钢的琴》《漫长的季节》的火爆收视率,变成了《尘土》《平原上的摩西》等畅销小说……
贾行家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的很多“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何40来岁失去工作就能陷入那样的境地。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东北人身强体壮,为什么不往南走一走,去打工呢?东北人为什么就不能出来呢?”
在贾行家看来,那是因为父辈那一代已经被塑造好了,“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要的不是自由,要的是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所以陷入了一种停滞。”
 贾行家作品封面。
贾行家作品封面。
但这反而给贾行家这一代的写作者们提供了空间,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回想,去思考。“毕竟,如果我在温州的话,肯定早就继承家族生意去了。”
最重要的是,亲历、目睹了这一切的东北二代们,身体、感受、记忆无法阻挡地在生长。当生长到再也无法压抑,自然就会发出让世界都听到的声音,这是贾行家的声音,也是那个时代一群人的声音。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祁倩倩





 投诉侵权
投诉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