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3日,是著名作家柳青逝世46周年纪念日。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为历史留下厚重的文学记录。不论书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著《创业史》,还是对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创作方法的身体力行,都是柳青为我们留下的不朽遗产。谨以此文,纪念柳青。
1943年元旦后的一天,柳青点燃一支边区的纸烟。此时,他纠结的心情,就像眼前大团大团化不开的浓雾。整风学习和支部工作的繁忙原本就使急迫的写作计划不断拖延,这时他又收到中央组织部调他到米脂县下乡的通知。
这次下乡的调动,是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的结果。对于《讲话》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号召,柳青心悦诚服,而且认为自己一直以来也是按照《讲话》的要求做的。就在这次调动之前,他才刚参与过米脂县印斗区乡选工作,并且已完成一部关于农民减租保佃斗争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他带着渴望写作的心情回到延安。
把之前深入生活得来的素材尽快写成小说才是当务之急啊,可是,在一纸调令面前,柳青不得不面对写作计划被打乱的现实,怎么办?“这一切就包含在工作之中”
作为一名党员,尽管怏怏不快,柳青还是拿着一封写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去米脂县报到了,并很快就被分配到一个乡政府担任文书工作。乡上的确是缺个文书。在柳青蹲点的三乡,连乡长常银占也不识字,他把上头要的统计资料、数字、汇报材料等一切动笔的事情统统交给柳青。入乡第二天,柳青就变成了一个大忙人,拖着一根打狗的棍子在几个村子间奔波。
乡里的实际工作远不止“动笔的事情”,真正沉入到具体工作,柳青才发现事无巨细,而且也真不简单。小到给村民写介绍信、割路条、调解纠纷,甚至操心娃娃头上疮的治疗;大到发动减租减息斗争、组织长期变工队、主持派粮工作、办联合学校、引导农民试种棉花等。米脂三年,与其说柳青是个作家,不如说更是一个地道的基层干部。
初下乡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让柳青有些应接不暇,工作局面打不开,也常令他一筹莫展。三四个月后,工作初见起色,柳青倍感兴奋。他兴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实际工作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阅历的浅薄,过往的生活体验和积累,对写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再回想起那个写减租保佃的长篇构思,是多么浮皮潦草的东西,庆幸没有把它写出来。如此一来,柳青这次下乡前的纠结和苦恼,也便烟消云散了。
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工作,柳青意识到深入生活的关键在于深入工作,不能像之前参加乡选工作那样只是为了搜集材料。搜集材料,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村具体工作的局外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单靠找人谈话、观察生活,是无法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情意相通的,更不能对乡村、农民真正熟悉和了解,这样即便能写出东西,也注定是浅薄、干瘪的,甚至可能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
“想写作,想学习,想锻炼自己,这一切都必须把工作做好之后,而这一切也就包含在工作之中。”这一认识,对柳青的写作生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当然知道相比于艰苦的乡下,延安有更好的写作条件,但更好的写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对写作最有利。他现在把实际工作看得重于一切,写作必须要与实际工作融合在一起。柳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他这一思想转折的产物。
“认真地在群众里生活”
《种谷记》是在大连完成的。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柳青被调赴东北做日军撤出后的接收工作。离开三乡时,几个干部把他送出米脂城。一路上,柳青满嘴说的都是眼下的秋收生产和学校的扩建工作,还有就是几家军烈属的安排和照顾工作。
从陕北到东北,路途波折,直到1946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柳青才抵达派驻的工作地,以主编的名义管理刚刚接收过来的鲶川洋行纸店,改为大众书店。已经在革命工作中历练了十年的柳青,在这里展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仅用两个月就让书店走向正轨,归书店管理的印刷厂昼夜不停地翻印解放区的革命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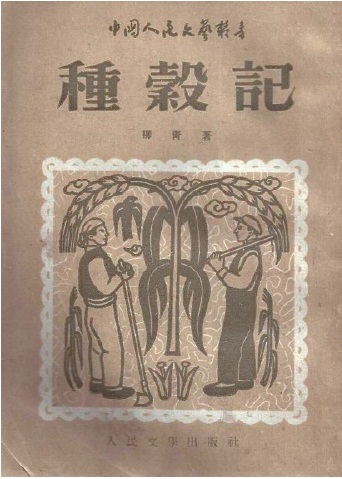
这段时间里,柳青难忘米脂三年的工作经历。实际上,《种谷记》在三乡时就已经开始动笔,他决定在大连工作期间完成这本书。
如果说到米脂下乡初期,柳青苦恼于工作繁重,没有时间写作。那么在大连期间,工作不仅清闲,生活环境相比三乡,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里,柳青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洋房,楼上楼下七八间屋,配有两部电话,房子里还安了一个四千度的电缸,冬天用来取暖。
在柳青的创作生涯中,没有再比写《种谷记》时更好的生活条件了。后来他回忆说:“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生活享受最高的时期。”
舒适的生活谁都喜欢,可是,柳青并不贪恋,反而充满警惕。出乎人们意料,1947年5月,《种谷记》一写完,他便决定回陕北,积累新的生活素材。这是一种苦行般的生活选择,因为柳青深知:“生活享受是要毁灭干部的”。他说:“当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小屋时,他就不愿意再到群众中去过艰苦的生活,或去了也急于想回到小屋……我清楚地感觉到许多同志三年五年以至十年八年没有作品,主要并非才能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在群众里生活。他们不是不想写出东西,而是极想写,只是没有解决了生活问题。我写了两本书就自满不再下去的话,我就完了。”
这就是柳青的个性,也是他的事业心。他认准了一件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早年在榆林中学念书时,曾因贪读文艺书籍,导致门门功课不及格,大哥一番电闪雷鸣的教诲,让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主业是什么,便开始发愤补习,开学后补考,竟得了第一名。后来学英文也是如此,点灯熬油,昼夜不休,刻苦到损伤了身体,导致咳血。现在柳青认准了深入生活这条写作道路,什么都阻挡不了他的步伐。刘可风在《柳青传》中对此有这样一个准确的比喻:“《种谷记》一完成,柳青就像在海浪中搏斗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货轮,终于到达目的地,卸完了船上的货物,他的头脑暂时空了。要继续写作,需要新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素材。他是一艘不能在码头上久留,随时整装待发的轮船。”
1951年初,周而复在上海组织了一场《种谷记》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巴金、李健吾、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魏金枝等名家。周而复和柳青原在延安共事,二人常一起谈论文学,颇为投契。组织这场座谈会,周而复的初衷是希望扩大《种谷记》在全国的影响,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与会者却批评多于赞扬。这给柳青极大的打击,但是冷静下来后,他很感激这次座谈会。因为参会的评论家们可都是深谙文学之道的内行,他们的不少意见还真是说中了一些要害。柳青意识到,克服缺点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唯一途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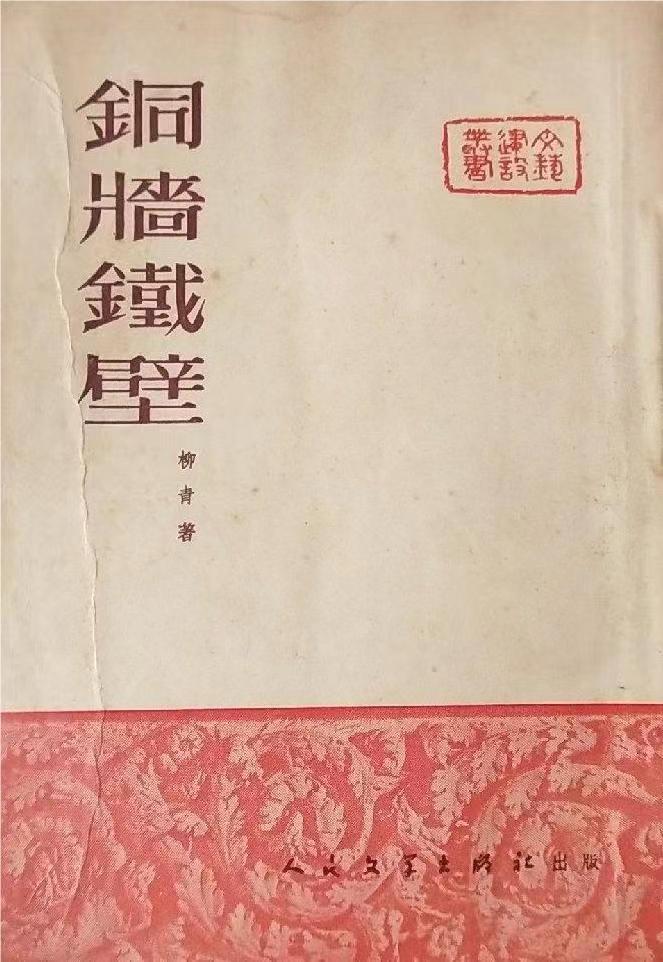
赞美有时可能扼杀一个作家,而兜头的冷水,也许会成就一个作家。没有在《种谷记》上遭遇滑铁卢,《创业史》或许未必能达到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度。可以推想,1952年柳青回陕西落户时,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他甚至有些急切地想离开当时正在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当然,不能说柳青再次下乡,是出于一己成败的考虑,还有更重要的一件即将开始的大事在吸引和鼓舞着他:中国农村即将展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经历了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况且,每个农民的经济状况不同,为了解决基础差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也为了避免农村再次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走合作化道路是大势所趋。从农村发展的长远看,从工农互补的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合作化道路也提供出一幅极为可期的社会主义美好图景。
柳青对时代精神高度敏感,他意识到这是当下最值得书写的题材,因为它将呈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可是,几千年来,农民已经过惯了一家一户的日子,穷了一家去乞讨,富了就自家享用,合作意识非常淡薄。再伟大的社会愿景,也必须从细枝末节的工作做起。1952年9月,柳青住进距西安二十五里的长安县县委大院,挂职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在对本县基本情况做充分地熟悉。
不曾想,柳青作为柳书记的一个为期十四年的人生阶段,就此开启。
作家应在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
米脂三年,让柳青认识到,深入工作才是深入生活的真正法门,只有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认识农村,熟悉农民。这对写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在1951年秋冬出访苏联期间,尤其访问雅斯纳雅·波良纳时,柳青所钟爱的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给了他新的启发,那就是作家应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
来到长安县,了解了本县的基本情况后,柳青迫不及待地进入村里,到农民中。半年来,王莽村是他去得最多的村庄。这个村“七一初级合作社”是全县建立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这里,柳青并不是一个来访者,而是实打实地作为柳书记展开具体工作。他召开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并且与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起制定了一个三年工作计划。
对于志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柳青而言,已经走在合作化前列的王莽村并非最合适的落户地。这时,正处于互助组阶段的皇甫村走入他的视野,而正是这里,成为后来《创业史》的“典型环境”。这个村刚刚入党的王家斌,就是《创业史》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出现的梁生宝的原型。

“春组织,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这四句话,说的就是在互助组的组织上,多数村子面临的相似困境。想靠互助组解决生产困难的农户很多,春荒时节便能纷纷组织起来,可一到农忙和秋收,大家又各自顾各自,不但失去了互助的凝聚力,还常常因为人心不齐而产生各种矛盾。皇甫村的王家斌所在的互助组却是一个例外,他领导的互助组近一年了,不但没散,还取得了丰产!
经过调研,柳青得知,王家斌所领导的互助组的六户人家之所以能组织起来,归根到底是因为都太穷。对于走投无路的庄稼人,互助组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之路,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合方式。另外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加入互助组,他们持观望态度,更不要说还有少数人对互助组持敌视态度,这些人往往经济基础较好,认为加入互助组会妨碍自己创立家业,对社会主义的远景也信心不足。这让柳青意识到,除了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思想教育也是农村工作中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组织开会、个别谈话、树立典型等,就成了柳青每日忙碌的重点。
引导农民参与改革,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很多干部容易犯讲大道理的毛病。柳青深知要深入农民,就要先做个农民。来皇甫村前,他就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换上一身对襟袄,把分头换成光头,不吸纸烟吸旱烟,看起来就和普通的关中农民无异。讲合作化的好处时,他会在场院、在草棚屋里讲,而且用农民愿意听的方式讲。吃过晚饭,村民们围坐在炕上,男人噙着烟袋锅,女人纳鞋底,地上的鞋东一只西一只。试想,农民累了一天,要是听大道理很快就盹得东倒西歪。可柳青幽默风趣,善于用农民的话讲农民的例子,有时候农民乐得前仰后合,有人还因此不小心打碎过一个米缸,这又引起一阵笑声。
王家斌后来这样回忆柳青的工作方式:“他对普通农民从来不发脾气,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和俺也要这样。他经常提醒我们做农民工作,说明问题时不要面面俱到,一次就讲一两个问题,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让人们真正理解党的政策,这也是他讲话的特点。”
“一头挑着生活,一头挑着技巧”
常到各户,柳青对每一个村民的思想、性格和语言特点,摸得很透彻。在地里干活时,人们也议论:“柳书记把咱这些人的脾气、心性摸得真清楚,咱这有事,谁可能有啥表现,说个啥话,他说得都差不离。”在皇甫村作为柳书记的柳青,是一个要时刻准备解决问题的人,从一个草棚屋出来,又进了另一个草棚屋。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农村中不同的人的思想方式、行为特点、语言风格,已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不断向前推动的同时,柳青也积累起丰富的创作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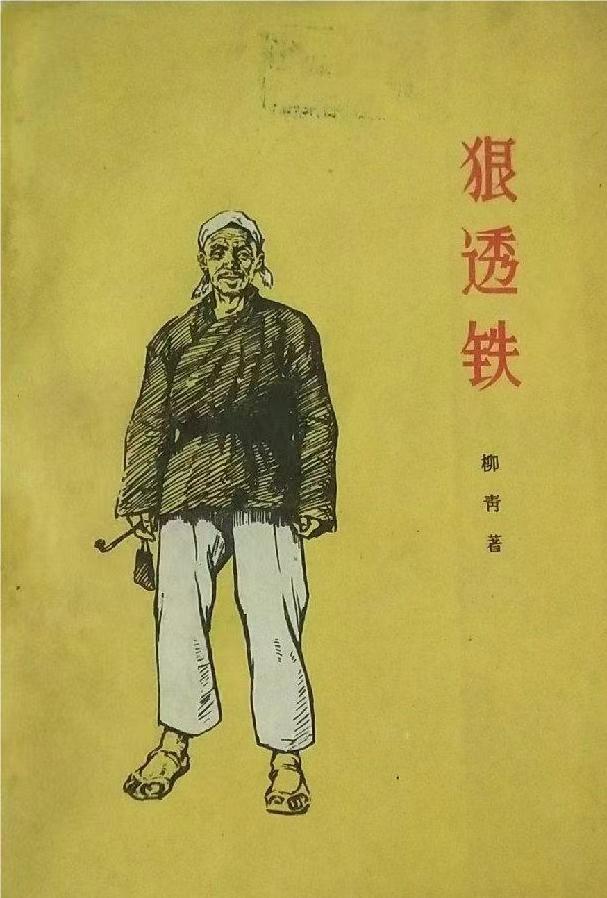
生活中,他也和当地农民一样上街赶集,提上筐,里面装着酱油瓶子,夹在人群中,和他们有说有笑。
赶集是观察农村生活的重要窗口,因此柳青几乎逢集必赶。在集市上,他是最忙碌的一个。跟着别人一起挤着排队,好容易排到门市前,却什么都不买,又挤出来重新排。他根本没打算买货,眼睛和耳朵却时刻保持紧张,关心排队的人们都在聊什么。有时,他还假扮粮客,把手放在牙家的凉帽下同他议价。
偶尔,柳青还会在集市外下棋。同别人一样,他也是戴着草帽,屁股下垫块石头。下棋的人中什么人都有,于是就有乡干部找区委书记孟维刚反映:“柳书记常教我们要划清阶级界限,他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大街上下棋。”他们不知道,柳青这哪里是在下棋呀。
不了解柳青的人,觉得这真是个怪老汉。可柳青心里满意极了,集市上的很多见闻和体验,对他的生活积累非常重要,其中很多都被搬到了《创业史》的场景中。实际上,不管是作为工作中那个严肃又有亲和力的柳书记,还是作为生活中那个朴素而偶显怪异的农村老汉,柳青毕竟是个作家,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1954年春,柳青的小说终于要开始动笔了。《创业史》的写作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多卷本大部头,如此宏大的创作野心,任是谁都难说不会望而生畏。柳青不是一个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反复研磨、过滤出来的”。写《种谷记》时,他曾说:“写文章比养娃娃还难。”
在《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过程中,他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什么样,但真正做出来却难如登天。写出的一稿、二稿,柳青都不满意,这让他非常痛苦。冥思苦想,一方面他认为是对生活的熟悉还是不够,还要深入了解人物。另外,从生活到作品,需要用文学技巧表达出来。所以他说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生活,一头挑着技巧”。技巧不到位,总让他觉着作品不动人。他反复思考,认为自己习惯性“用作者的感觉代替人物的感觉”。
1958年,柳青开始了第三稿的写作。这时,他像演员演戏一样“入戏”,进入不同的角色,让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行动都变成人物本身的,而不是作者在叙述。
这种写作方式,如他做柳书记做工作、做农村老汉去生活时的方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成为农民。
在漫长的写作岁月中,很多人对柳青产生过质疑:“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既然我决心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真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为完成《创业史》的写作计划,柳青真是拼了命,创作的苦恼常常折磨着他。有时写作遇到不熟悉的内容,比如写“题叙”时,他便常常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有时,老人正说在兴头,柳青转身就走,思路茅塞顿开让他恨不得立刻飞回书桌前奋笔疾书。这弄得老人莫名其妙,小声嘀咕:“这人有神经病呢。”
柳青沉浸在创作状态时,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个完全没法理解的“怪”老汉。而创作的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身体反映着柳青写作时的焦灼,左腿内侧长出了疮,几个月后鸡蛋大,后背又出来一个痈,脓血不断。光“题叙”一章,竟写了八个月。修改过程,有的章节用新的手法写一遍,有的章节则反复重写。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终于写成了!先在《延河》连载,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稿费一万六千多元,柳青分文没留,全部捐给本地做建设。这本书的好评不断很快吸引了大批记者来访,柳青不愿为此分心,定出一个“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介绍经验。因为他知道,写作是他的使命,“宣传对我的工作没有益处”。
他要保持写作的状态,就要始终在人民中扎根,这也是柳青对自己的要求:“一生都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柳青简介

柳青(1916年7月2日—1978年6月13日),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中篇小说《狠透铁》,短篇小说集《地雷》。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1943年,到陕西省米脂县三乡任乡政府文书。抗战胜利后,到大连大众书店做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8月,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扎根皇甫村深入生活十四年,完成《创业史》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业史》于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作者:石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





 投诉侵权
投诉侵权